我留意这家人已有一段时日了。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个褓母,就靠她替别人照顾孩子和外家少少的补贴,生活才能维持下去。住在这里非法木屋区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至于两个孩子的父亲呢?
“有外遇? 还是 故意撇下两个子女不管了?”陈太太一脸疑惑。
“哎呀!你不知道吗? 听说阿莲的丈夫前年在外头已有了另一个家呢!”黄太太表情肉紧地接着说。
“阿莲就是命苦罗!两个小丫头才七、八岁,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样样都要钱。”
“呃,阿莲的住家不是有房间出租给几个印尼人吗?我想经济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吧?”陈太太又问。
“陈太太不说你不知,那是她丈夫租出去的,几时轮到她作主收租嘛,唉!”黄太太摇摇头在叹气。
黄太太接着又苦笑说“认命吧!谁叫你是女人!”
八婶操着半咸不淡的广东话拍着陈太太的肩膀说:“好的就是男人,不好的就是难 忍啊!”
两个孩子的父亲引起了我的注意,可能他是和我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极为相似吧!
自从父亲离开我们后,母亲就变得沉默憔悴。小时候,每当我向母亲问起父亲时,她就不断流泪,而且每一次总是对我重复同一句话:“少芬,你爸爸不会再回来看你了,你认命吧!”母亲对一个忠心不二的丈夫已没有指望了,更何况是当女人为了寡情的男人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时,我也开始知道父亲离我越来越远……
我总是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看到我的过去。
每当出外时总会有多事的人在我身上指指点点,我就像那两个孩子一样,心里蛮不是滋味的。我很想大声地告诉他们:“不是我的错,是父亲的错啦!”但每次我只敢低下头看着自己寒酸的鞋子,一肚子的气就此怪在父亲的身上。我开始讨厌父亲了,正如那两个孩子的眼神一样倔强又失意。可是最终还是要被旁人问到一头雾水。“你父亲上了哪儿?”或是“你父亲不要你啦!”
我逐渐记起那些不愉快的过去。小时候家境穷要靠小小的鱼档维生,小小年纪的我就要在鱼档帮头帮尾。有一回,觉得自己真的再也忍不住那些围在身上久久挥不去的鱼腥味,结果我逃跑了出来。我到处乱跑,在草场上吹吹风、看小鸟飞翔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……那应该是我童年时最美丽的回忆了。那天回家后我还捏了一个谎话骗母亲,最终还是被她识穿了。母亲毫不留情地鞭打我,到了晚上还声色凝重地对我说:“你要我学你父亲一样丢下你不管是吗?你想做孤儿是不是?你尽管骗我,尽管变得像你父亲一样骗我……。说!你快对月亮娘娘说,以后你不敢再说谎 了!”
我依稀记得我流了两行眼泪拉着耳朵对月亮说:“我不敢说谎了,我不要做孤儿,我要妈妈!”其实心里却一直想着,我是不是该继续骗自己说,不再想爸爸了。其实我生活得一点也不开心啊!就像那一年的中秋节,我连一块豆沙月饼也没吃到。我就是在这样是非恩怨尖锐对立、非黑既白的教育之下长大了。
后来父亲回来了,也是在某一个中秋节的晚上。
“妈,你还恨不恨爸爸?”我蹙紧眉头问母亲。母亲在那个时候只说了一句我似懂非懂的话:“如果我始终觉得自己是赤贫的,就算上帝给了我一切,我还是穷的……。”我还问母亲为什么不跟父亲说话,母亲一直都没有回答我。父亲一直相对母亲弥补过去的错。虽然多年以来做出了种种的忍让和补偿,可是母亲临死也不领他的情。母亲一直错看了她心爱的男人,她以前认为他是个忠诚的丈夫,结果父亲却做了对不起她的事;待父亲浪子回头了,她却以为他是带着某种企图而回来的。想不到母亲把自己一辈子的错误也带入土去了。父亲非但没有把我卖出去,还在母亲去世后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
母亲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晚上逝世的,死前也没对父亲瞧上一眼。母亲依然执着于她那一套非黑既白、不爱就是恨的教育。我想我是叛逆的,我不爱听母亲的训话,我
不喜欢那套教育,我明白很一个人不容易。自从母亲走后,我常常幻想自己是个孤儿,因为这样我才会更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辗转之下,我和父亲搬来这个非法木屋区已有两年多了。
父亲变得苍老了,有时还兀自躺在木藤的老人椅上,看着夕阳下山。有时他想起了母亲就在喃喃自语,好像重复多年前的一句话:“阿兰,请你原谅我”。
一直到这个世纪末的中秋节晚上,我在放工后就陪着父亲赏月、吃着自己心爱的豆沙月饼。赏过月不久后,我被一道七彩绮丽的灯光吸引住了。原来是一个男人一边提着灯笼一边驾着摩多。“咦!那个摩多骑士不就是阿莲的丈夫吗?”我心里暗忖。“爸爸!爸爸!我们的飞机灯笼!”两个孩子已迫不及待地喊叫跑了出来。
“怎么少了一对飞翼的?”阿莲也跟了出来问。经阿莲这么一问,我才发现那个飞机模型的灯笼真的是少了一对飞翼,像是缺了一些什么似的。
“来不及啦!廖师傅说要赶回去次团圆饭呢!”阿莲的丈夫忙着说。
我在想,这有什么关系呢?反正阿莲已原谅了她的丈夫,听黄太太说他的丈夫已修身养性了。
“妈,你看月亮又圆又亮哦!”孩子还在叫嚷个不停。
“又圆又亮……圆……亮”乍听之下似是原谅一词,原谅一个浪子回头的丈夫,原谅一个浪子回头的父亲。我怔怔地望着自己身边的父亲,突然觉得自己还是幸福的。
摘自星洲日报《城人小说》 27.10.199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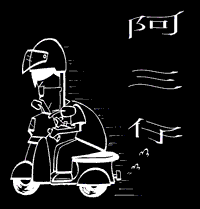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